陈砚把周慧萍递来的单据推回桌角,没再多看一眼。他站起身,白大褂下摆蹭过桌沿,左手插进裤兜,指尖碰到那卷从杂物间拿来的电源线。周慧萍还在说什么,声音有点高,但他没听清,只看见她嘴皮动了两下,转身走了。

走廊灯亮着,和刚才一样。
他走出值班室,脚步没停,径直往一楼大厅走。清晨六点十七分,急诊科刚交完班,人少了一半。清洁工推着车从拐角出来,不锈钢桶边挂着塑料袋,轮子卡了块口香糖,走一步响一声。
陈砚在自动售货机前停下,投币,按下“肉包+豆浆”。机器嗡了一声,托盘滚出一个纸袋。他拿起来,没急着吃,靠在墙边,低头咬了一口。肉馅凉的,面皮有点硬,他一边嚼一边抬眼,视线扫过清洁车后轮上方——三厘米见方的黑色方块贴在车架内侧,镜头朝下,正对着抢救室门口的动线。
他没动,继续啃包子。
昨天周慧萍说系统记录他刷了卡,可他没进过药房。监控被改过,这他知道。但改数据的是人,装摄像头的也是人。现在这台设备不在安防系统名录里,线路独立,信号不走主网,显然是私装的。谁会把监控安在清洁车上?只有想绕过登记、随时移动追踪的人。
他吃完最后一口,把纸袋揉成团,朝垃圾桶扔去。偏了,落在桶外。他没去捡,转身往回走,路过清洁车时脚步慢了半拍,右手扶着车把借力,左手下垂,指尖顺势在车底一划——胶贴边缘有毛刺,是新粘的,还没干透。
他继续往前,像什么都没发生。
十分钟后,他蹲在护士站对面的饮水机旁,拧开瓶盖接水。余光里,周慧萍从走廊那头走来,手里抱着一摞病历,鞋带松了,拖在地上。他站起身,迎上去两步,开口:“护士长,你鞋带散了。”
周慧萍低头看。
就在她弯腰的瞬间,陈砚右脚往前半步挡住她视线,左手从裤兜抽出,袖口一垂,手指已探到车底,指甲一抠,内存卡脱落,落入掌心。他顺势弯腰,右手作势去扶她胳膊,实则将卡片夹在中指与无名指之间,一转手,滑进左脚鞋垫内侧。
动作没停,他直起身,把水瓶递过去:“喝点?”
周慧萍直起腰,接过瓶子,拧开喝了一口,“谢了。你刚才蹲那儿干嘛?”
“捡瓶子。”他说。
“哪个瓶子?”
“就刚才扔的那个。”他指了指垃圾桶外的纸团,“懒得弯腰,踢了两下没进去。”
周慧萍皱眉,“你这人......能走两步就走两步,非得踢?”
他没答,抬手摸了摸后颈,像在挠痒,实则借这个动作扫了一眼头顶的监控探头。镜头正缓缓转动,扫过清洁车,停顿半秒,又移开。
他转身往茶水间走。
里面没人。他拉开冰箱门,拿出一盒牛奶,撕开喝了一口,靠在门边,用脚尖轻轻碾了碾左脚鞋跟。卡片在足弓内侧,贴着袜底,不硌,也不滑。金属探测仪过脚踝时不会响,手检也难摸到——鞋垫厚,又是旧款,没人会特意翻。
他把牛奶盒捏扁,扔进可回收桶,走出茶水间。
走廊安静,保洁车停在原地,清洁工去了别处。他路过时,看见那台微型摄像头依旧亮着红灯,一闪,一闪,像呼吸。
他没再看,拐进男厕。
隔间里,他脱下左鞋,掀开鞋垫,取出内存卡。指甲大小,黑色,表面无标识。他对着灯看了两秒,没插进手机,也没放回口袋,而是撕下一张手纸,包住卡片,塞进内裤前袋。那里不会被搜,也不会被查。
穿好鞋,他洗手,抬头看镜子里的自己。脸还是那张脸,头发乱,眼眶发青,像熬了一夜。他抹了把脸,走出去。
回到值班室,他拉开抽屉,翻出一张空白排班表,撕下一角,在上面写:“清洁车,三号位,独立电源,信号未入主网。”字写得潦草,像是随手记的交接事项。写完,他把纸片揉成团,扔进垃圾桶。
桌上的备用机亮了一下,短信震动。
他拿起来,没解锁,直接关机,取出SIM卡,用指甲掰断,扔进废纸篓。
然后他坐下,翻开病历本,翻到一页空白,写:“X7批号肾上腺素,未使用,系统记录异常。”写完,合上本子,推到桌角。
十分钟后,王振海从走廊经过,脚步没停,但眼角扫了一眼值班室。门开着,陈砚坐在里面,头低着,手里拿着笔,像是在写什么。
他没进去。
陈砚也没抬头。
王振海走远后,他把病历本重新打开,翻到刚才那页,用笔在“未使用”三个字下面划了一道线,又在旁边写了个“查”字,但最后一笔没收尾,断在纸上。
他放下笔,伸手摸了摸左脚鞋垫。
卡片不在了,但脚底还留着一点硬物压过的痕迹。

![咸鱼医神完结_[陈砚周慧萍]后续无弹窗大结局](https://image-cdn.iyykj.cn/2408/57fd4129b8d867e915495a4f1f86aaff.jpg)

![[死后第五年,老公为救恩人再次典当我的寿命]小说全文txt完整版阅读-胡子阅读](https://image-cdn.iyykj.cn/2408/e3b89c0bd42dbca3e965fd6ace8b4efe.jpg)
![[人间捉鬼师]最新章节列表_[江浔才]完结-胡子阅读](http://image-cdn.iyykj.cn/0905/aec379310a55b3194e437e32e7c86b2acefc17a9.jpg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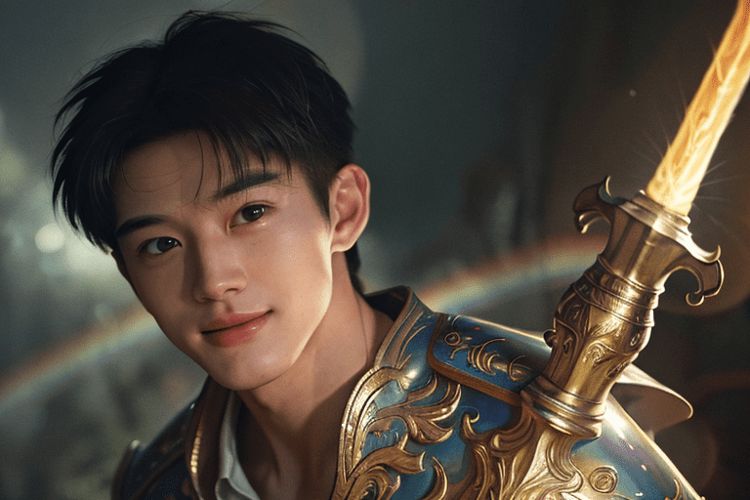
![[师妹魂飞魄散后,我怒开第十九层地狱]最新后续章节在线阅读-胡子阅读](https://image-cdn.iyykj.cn/2408/ae0584c6e356b31905cc2d2a3d91f206.jpg)